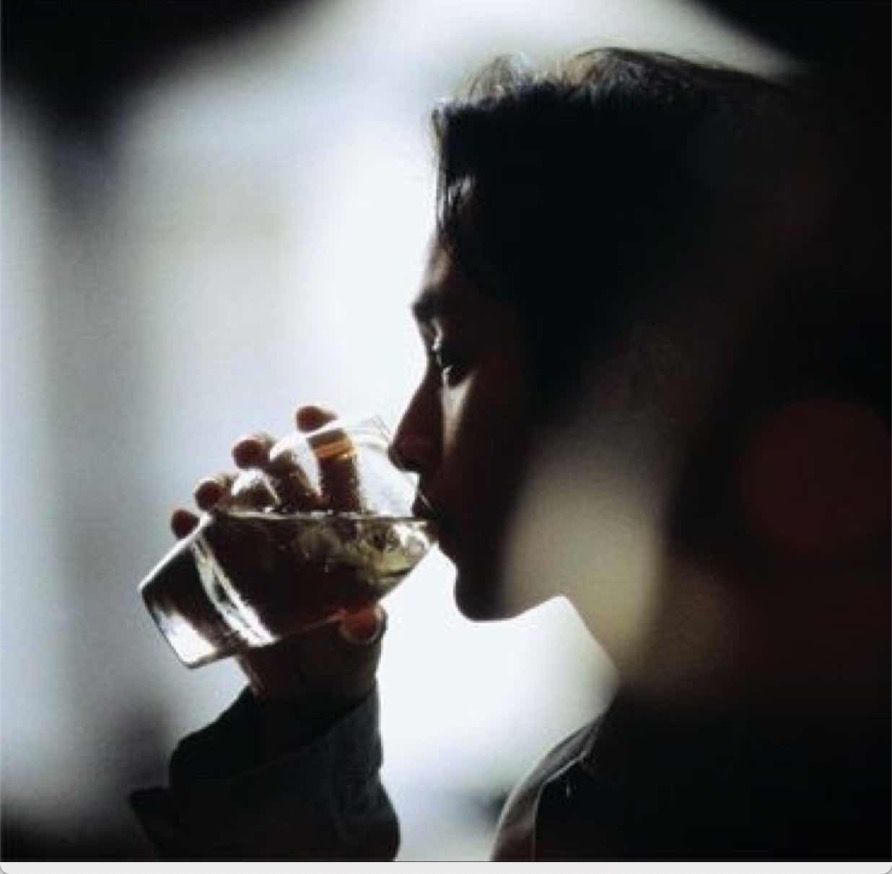懒了大半个月再来回忆丽江,初遇的魅惑已经沉淀凝固,变成了一幅不褪色的油画,让我能在回忆里默默地注视和微笑。
清早,从酒店的窗户向外望,玉龙雪山原来早就醒了,在15公里之外远远地向我说早安。
 本来是要坐小索道上云杉坪,再逛逛白水河的,但是前一天司机告诉我们,小索道的上下落差只有4米,那里没有雪,很没意思的,大索道倒是能上到海拔4500米样子,但是需要提前预约。想来想去,我们放弃了登雪山,这次就只在山脚下转转吧。
本来是要坐小索道上云杉坪,再逛逛白水河的,但是前一天司机告诉我们,小索道的上下落差只有4米,那里没有雪,很没意思的,大索道倒是能上到海拔4500米样子,但是需要提前预约。想来想去,我们放弃了登雪山,这次就只在山脚下转转吧。
就去了雪山主峰南麓的“玉柱擎天”。在我看来,“玉柱擎天”也没什么,无非是几百年前两个文官儿为了显摆自己的地位和才艺,在大石头上刻的大字而已。只是风吹雨淋了几百年,到如今还看得分明,倒也有点难得;
在石崖下有一潭水,名叫“玉湖”。玉湖里的每一颗水滴,都曾经是5800米高处的一片雪花。
玉湖不算大,称不上大气滂沱,但是它禀承了峰顶的冰雪之质,山光水色,上下空明,连波澜都是矜持的。
玉湖倒影,是玉龙雪山十二影之首。蓝天白云在水面缓缓游移,垂枝和野草倒生在水下,轻微晃动,偶有一两条活泼的红鳟鱼不小心碰碎掉这些景致,一双好脾气的大手安抚着,安抚着,耐心地把细碎的图画再一块一块重新拼好。
比起滇池和洱海,这里更安静,更温婉,以致于看着看着,突然想不起时间是个什么东西。
 不知道是因为台阶客观上确实够高够陡,还是传说中的高原反应,总之在冲击3200米高地的时候,我有点上不来气。
不知道是因为台阶客观上确实够高够陡,还是传说中的高原反应,总之在冲击3200米高地的时候,我有点上不来气。
即便这样,形式上还是要藐视一把的,以便在下次上4000米的时候不至于心虚。
 走下石阶,向远处看,一个纳西小村落舒适地窝在层叠的翠色里,院墙甚至都不加雕饰,就用石料顺其自然地那么一堆——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龙山下第一村–白沙玉湖村。有个叫洛克的奥地利学者,曾经就以这里作为他研究东巴文化的起点,从此深深沉迷。
走下石阶,向远处看,一个纳西小村落舒适地窝在层叠的翠色里,院墙甚至都不加雕饰,就用石料顺其自然地那么一堆——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龙山下第一村–白沙玉湖村。有个叫洛克的奥地利学者,曾经就以这里作为他研究东巴文化的起点,从此深深沉迷。
在见到丽江之前,我对它有千百种的想象,想象它的浓艳,想象它的散漫,想象它一地金光灿灿的太阳。在见到丽江之后,才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似是而非,却又太过单薄。
真的,这是一个很难用文字描摹清楚的地方。有太多种文化和情绪在这里相交碰撞,新的,旧的,本土的,外来的,民族的,世界的。大都市的浮华锐利在这里化成了轻飘飘的水蒸气;盒子们的忙碌怨尤在这里成了最无趣味的庸人自扰。在这里,CHLOE的风头抢不过颜色多得简直不符合美学规则的手绣布包;一只不做雕饰的宽扁银镯,硬是要远比TIFFANY红透全球的大师设计更来得无限风情。
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,价值观念,在这里,在干净得不带一丝杂色的高原阳光里,轻而易举就消融至无形。

 成千上万的愿望挂在一起。风吹过,铃声清脆悦耳,无数的愿望幻灭又升起。
成千上万的愿望挂在一起。风吹过,铃声清脆悦耳,无数的愿望幻灭又升起。
在古镇,水流不只是水流,它还有特殊的意义:顺水进城,逆水出城。它按这条定律指引着过往的脚步,指引了上千年。






 茶才刚刚沏上,第一缕热的气息才刚刚舒展,日光才刚刚攀上窗台,一天中的好时光就要开始——在温暖的阳光里眯起眼睛,轻轻抿一口新茶,想,或者什么都不想。
茶才刚刚沏上,第一缕热的气息才刚刚舒展,日光才刚刚攀上窗台,一天中的好时光就要开始——在温暖的阳光里眯起眼睛,轻轻抿一口新茶,想,或者什么都不想。
在这里,生存很简单,快乐很简单。
生活,原来,竟然,还可以这样。

黑暗中,安静和喧闹有着固定的分界线,四方街外是安静的,水,树,天上的月亮,都慈悲地静默着;沿街的小铺安静地亮着灯,店主安静地坐在柜台后面看着你;沿着水随意地走,小声的闲语也不用担心对方听不清。对面不时有人三三两两地过来,但是天南地北,互不相识,没有人问你的过去,也没有人着急你的将来。在这里,耳朵很安静,心则可以更安静。
但是一拐入四方街,仿佛全世界的喧闹和热量全部都汇聚来了,整整一条街都在沸腾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地方,比这里更随性,更肆意。坐在椅子背上,坐在窗台外面,坐在水边,站在门廊下面,大声地笑,一群一群,认识或者不认识,隔着水,甚至隔着街,此起彼伏地对歌,不管什么歌,只要是想得起来,唱得出来的,只唱一小段,用力地晃着腿,挥着胳膊,叫完“呀索呀索呀呀索”,对面的接着唱另外一首,接不上来就会被善意地笑闹。时不时有新人加入,也会有人离开,但无论是新来的还是离开的,都不会受到阻止。甚至酒吧里的伙计,也会一边倒着酒,一边扯着嗓子跟自己店的客人一起唱。四方街,它简直就不打算给你留一点点寂寞的空间。
总之,这就是夜晚的丽江,淡淡的酒,淡淡的萍水相逢,热闹的人可以在足够的旖旎里肆意狂欢。而安静的人在幽深的巷子,小小的院落里,看浩浩星空,仍听得见风掠过屋檐时的私语。








 回来已经有些天了,但是一念起“丽江”这两个字,仍然会有一丝的恍惚。我对它的怀念是纯粹的,所以并不容易说出来,因为我不懂得该如何说。
回来已经有些天了,但是一念起“丽江”这两个字,仍然会有一丝的恍惚。我对它的怀念是纯粹的,所以并不容易说出来,因为我不懂得该如何说。
丽江,我想,我应该,也许我必须会再去——去寻找,或者去颠覆。